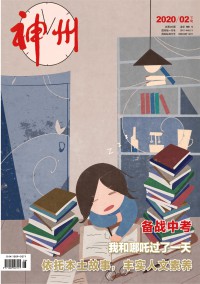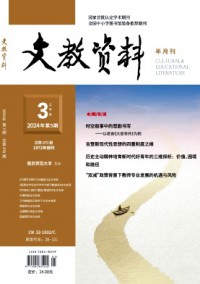语言与文化关系论文汇总十篇
时间:2022-12-02 12:23:02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语言与文化关系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肝纤维化是现代医学病理形态学的概念,常由于肝内慢性炎症,胆汁郁积,免疫损伤等原因引起,中医学并没有肝纤维化的名称,但根据该病的临床表现,多归属于中医的“黄疸”“胁痛”“积聚”等范畴,目前西药对该病没有特效药,而中医中药对该病有着较好的优势和疗效,且慢性乙型肝炎在我国人群中普遍存在,更是引发肝纤维化的主要原因。因此,对肝纤维化的中医发病机制的探讨有着重要的意义。
1中医对痰淤的认识
痰是中医病理学中的重要病理产物。痰最早见于《金匮要略·痰饮咳嗽病脉证并治》:“膈上病痰满喘吐。”仲景将痰饮列为四饮证之一。隋唐至宋代痰已成为独立病症。唐·孙思邈的《千金方》温胆汤、宋·陈师文的《和剂局方》二陈汤已为治痰的经典方剂。至明清,痰的理论进一步深入,痰生百病。“百病多兼痰”已成为众多医家之共识。在辨证上有内痰与外痰,有形痰与无形痰之分,在治法上有健脾补肾、利气化痰等多种见解。痰为津液不归正化而形成的病理产物,其产生与脏腑气血功能失调密切相关,外感邪气、内伤情志或脾肾亏虚均可导致机体水湿停聚,或热灼伤津聚均可成痰。
淤亦是中医病理学中的重要病理产物。中医认为,淤血指体内有血液停滞,包括离经之血积存于体内,或血运不畅,阻滞于经脉及脏腑内的血液,均称为淤血。《内经》虽无“淤血”但有“恶血”“血菀”“留血”等近似淤血的名称30余种,其对血淤证的成因、症状也有明确的阐述,“输其血气,令其条达”为治淤法则。《神农本草经》也有了活血化淤药的记载,汉代以后,张仲景总结了血淤证的辨证规律,其在《金匮要略·胸痹心痛短气病脉证并治》认为痰饮乃胸痹的病机之一,治则以除痰通阳为主。隋唐至金元血淤证的理论阐述与治疗方剂进一步发展。明清医家在继承了前人的学术思想上又有深入的研究,张介宾提出了“气逆而血留,气虚而血滞,气弱而血不行”,丰富了血淤证理论。比较突出的是王清任,他强调气血为人之本,处方用药思路更为广阔,指出治胸痛用木金散,若无效则需用血府逐淤汤。其治疗胸痛倡用活血祛淤的治则,颇具独创精神,创立祛淤诸方,扩大了活血化淤法的治疗范围,使血淤证与活血化淤的理论更加完善。
对痰与淤的关系,历代医家认为:痰是津液的病变,淤是血的病理形式,二者关系密切,中医学关于痰淤同病,痰可致淤的认识,渊源甚早。《灵枢·百病始生》指出:“湿气不行,凝血蕴里而涩渗,著而不去,而积皆成矣”;《丹溪心法》谈到:“痰夹淤血,遂成窠囊”,强调痰中夹淤这一病理在致病中的广泛性和重要性。《外证医案汇编》分析道:“流痰,蓄则凝结为痰,气渐阻,血渐淤,流痰成矣。”《血证论》中的“须知痰水之壅,由淤血使然,但去淤血,则痰水自消”,“血积既久,亦能化为痰水”。由于津血同源,所以痰淤不仅互相渗透,而且可以互相转化,因痰致淤,或因淤致痰。
2痰淤阻络是肝纤维化的重要病机
一般认为,肝纤维化的中医病因多为感受湿毒疫邪,肝气郁滞,肝肾亏虚等,导致脏腑功能失调,痰浊淤血阻滞肝脉而逐渐形成肝纤维化。其中,痰淤阻络是肝纤维化的病理基础。临床发现,肝硬化病人多伴有肝掌,蜘蛛痣,肝脾肿大,舌质紫暗或有淤斑,脉涩等症,这些均为血淤的临床表现。除此之外,血淤在肝纤维化中与肝脏微循环、肝纤维化结缔组织增生及肝功能指标都有密切相关性[1],刘宏元等[2]结合现代病理学指出,肝细胞及血窦内上皮细胞的坏死变性,引起肝组织微循环障碍而产生血淤证,同时贮脂细胞及肝细胞增生分泌大量胶原蛋白,形成胶原纤维束,逐渐发展为肝纤维化也形成血淤证。可见,淤血在肝纤维化中的病理表现为肝脏微循环障碍及纤维结缔组织增生,并始终存在于肝纤维化过程中。大量研究结果同样表明:肝血淤阻程度与肝纤维化程度密切相关,并进一步指出血淤证患者血清型前胶原(PCIII)、透明质酸(HA)、层黏蛋白(LN)均比非血淤证患者明显增高,肝纤维化血清标志物PCIII,HA,LN可作为血淤程度的客观指标[3,4]。另有学者通过实验研究得出了相似结论:血淤证肝病患者血清总胆红素(TBIL)升高及A/G降低显著高于非血淤证肝病患者,血淤证肝病患者血清HA,LN明显高于非血淤证肝病患者及正常人,提示A/G下降或倒置及血清HA,LN的含量可作为慢性肝病血淤证辨证的客观指标[5]。
【摘要】归纳中医关于痰淤理论的学说,探讨了痰淤与肝纤维化的密切关系,提出痰淤阻滞肝脉是肝纤维化发生发展的重要病理因素。
【关键词】痰淤肝纤维化
肝纤维化是现代医学病理形态学的概念,常由于肝内慢性炎症,胆汁郁积,免疫损伤等原因引起,中医学并没有肝纤维化的名称,但根据该病的临床表现,多归属于中医的“黄疸”“胁痛”“积聚”等范畴,目前西药对该病没有特效药,而中医中药对该病有着较好的优势和疗效,且慢性乙型肝炎在我国人群中普遍存在,更是引发肝纤维化的主要原因。因此,对肝纤维化的中医发病机制的探讨有着重要的意义。
1中医对痰淤的认识
痰是中医病理学中的重要病理产物。痰最早见于《金匮要略·痰饮咳嗽病脉证并治》:“膈上病痰满喘吐。”仲景将痰饮列为四饮证之一。隋唐至宋代痰已成为独立病症。唐·孙思邈的《千金方》温胆汤、宋·陈师文的《和剂局方》二陈汤已为治痰的经典方剂。至明清,痰的理论进一步深入,痰生百病。“百病多兼痰”已成为众多医家之共识。在辨证上有内痰与外痰,有形痰与无形痰之分,在治法上有健脾补肾、利气化痰等多种见解。痰为津液不归正化而形成的病理产物,其产生与脏腑气血功能失调密切相关,外感邪气、内伤情志或脾肾亏虚均可导致机体水湿停聚,或热灼伤津聚均可成痰。
淤亦是中医病理学中的重要病理产物。中医认为,淤血指体内有血液停滞,包括离经之血积存于体内,或血运不畅,阻滞于经脉及脏腑内的血液,均称为淤血。《内经》虽无“淤血”但有“恶血”“血菀”“留血”等近似淤血的名称30余种,其对血淤证的成因、症状也有明确的阐述,“输其血气,令其条达”为治淤法则。《神农本草经》也有了活血化淤药的记载,汉代以后,张仲景总结了血淤证的辨证规律,其在《金匮要略·胸痹心痛短气病脉证并治》认为痰饮乃胸痹的病机之一,治则以除痰通阳为主。隋唐至金元血淤证的理论阐述与治疗方剂进一步发展。明清医家在继承了前人的学术思想上又有深入的研究,张介宾提出了“气逆而血留,气虚而血滞,气弱而血不行”,丰富了血淤证理论。比较突出的是王清任,他强调气血为人之本,处方用药思路更为广阔,指出治胸痛用木金散,若无效则需用血府逐淤汤。其治疗胸痛倡用活血祛淤的治则,颇具独创精神,创立祛淤诸方,扩大了活血化淤法的治疗范围,使血淤证与活血化淤的理论更加完善。
对痰与淤的关系,历代医家认为:痰是津液的病变,淤是血的病理形式,二者关系密切,中医学关于痰淤同病,痰可致淤的认识,渊源甚早。《灵枢·百病始生》指出:“湿气不行,凝血蕴里而涩渗,著而不去,而积皆成矣”;《丹溪心法》谈到:“痰夹淤血,遂成窠囊”,强调痰中夹淤这一病理在致病中的广泛性和重要性。《外证医案汇编》分析道:“流痰,蓄则凝结为痰,气渐阻,血渐淤,流痰成矣。”《血证论》中的“须知痰水之壅,由淤血使然,但去淤血,则痰水自消”,“血积既久,亦能化为痰水”。由于津血同源,所以痰淤不仅互相渗透,而且可以互相转化,因痰致淤,或因淤致痰。
2痰淤阻络是肝纤维化的重要病机
一般认为,肝纤维化的中医病因多为感受湿毒疫邪,肝气郁滞,肝肾亏虚等,导致脏腑功能失调,痰浊淤血阻滞肝脉而逐渐形成肝纤维化。其中,痰淤阻络是肝纤维化的病理基础。临床发现,肝硬化病人多伴有肝掌,蜘蛛痣,肝脾肿大,舌质紫暗或有淤斑,脉涩等症,这些均为血淤的临床表现。除此之外,血淤在肝纤维化中与肝脏微循环、肝纤维化结缔组织增生及肝功能指标都有密切相关性[1],刘宏元等[2]结合现代病理学指出,肝细胞及血窦内上皮细胞的坏死变性,引起肝组织微循环障碍而产生血淤证,同时贮脂细胞及肝细胞增生分泌大量胶原蛋白,形成胶原纤维束,逐渐发展为肝纤维化也形成血淤证。可见,淤血在肝纤维化中的病理表现为肝脏微循环障碍及纤维结缔组织增生,并始终存在于肝纤维化过程中。大量研究结果同样表明:肝血淤阻程度与肝纤维化程度密切相关,并进一步指出血淤证患者血清型前胶原(PCIII)、透明质酸(HA)、层黏蛋白(LN)均比非血淤证患者明显增高,肝纤维化血清标志物PCIII,HA,LN可作为血淤程度的客观指标[3,4]。另有学者通过实验研究得出了相似结论:血淤证肝病患者血清总胆红素(TBIL)升高及A/G降低显著高于非血淤证肝病患者,血淤证肝病患者血清HA,LN明显高于非血淤证肝病患者及正常人,提示A/G下降或倒置及血清HA,LN的含量可作为慢性肝病血淤证辨证的客观指标[5]。
此外,痰湿在肝纤维化中亦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现代医学研究认为,中医痰证的主要特征和生化物质基础为血清总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的升高[6],而由肝纤维化导致的肝筛失窗孔化,毛细血管化,肝窦紊乱短路等肝内微循环障碍亦影响肝内脂类代谢,且有资料研究显示肝脏功能轻、中度损伤时血脂水平与肝纤维化血清学指标呈正相关[6]。因此,血脂水平及肝内血流速度可作为肝纤维化痰淤互结证的疗效判定指标。刘为民等[7]认为肝纤维化除淤血外,痰浊作为一种病理因素,也参与了肝纤维化的病程。在肝纤维化的发病过程中,肝郁气滞,横逆犯脾,脾失健运,水湿不化,酿生痰浊;饮食所伤,素体湿盛,嗜甘厚腻,过度饮酒,更伤脾胃,水湿内停,聚为痰饮;正虚邪恋,毒邪内蕴,日久化热,煎熬津液,凝聚成痰;正气亏虚,水湿难运,聚湿成痰,均可导致痰浊内生,痰淤互结,阻于肝络。因此痰浊淤血是肝纤维化的最终病理产物,同时又可阻滞气机,使气血运行不畅,津液输布不利,痰浊淤血沉积更甚,加速肝纤维化的发生发展。陶翠玲等[8]以痰淤并治为主要治疗原则,应用肝纤康治疗慢性病毒性肝炎肝纤维化痰淤互结证,结果表明该方具有降低痰淤互结证积分水平,降低肝纤维化血清学指标,抑制肝脏炎症,改善肝功能,增加肝门静脉血流速度,降低甘油三酯水平的作用。并认为其治疗机理可能是降低血脂,改善肝脏微循环,增加肝脏血流速度,抑制和改善炎症反应,改善肝功能,从而阻止和减慢肝纤维化的启动和发展过程。
3结语
在肝纤维化的发病过程中,血淤与痰湿又相互伴生及互为因果。淤血阻络,必阻碍气机,气机阻滞,津液不布,水湿不化,而聚湿生痰;同理,痰湿阻络,亦必阻碍气机,血为气之母,气为血之帅,气机阻滞,血行不畅,而致淤阻经络,从而导致肝纤维化的发生发展。
【参考文献】
[1]唐智敏,茹清静,朱起贵.论肝血淤阻与肝纤维化的关系[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1996,2(3):14.
[2]刘宏元,刘作恩.慢性乙肝早期纤维化的治疗研究[J].天津中医,1997,14(3):101.
[3]陈丽萍,张诗军,马翠玉,等.慢性丙型肝炎血淤证与血清HA、hPCIII的相互关系及中药对其影响的研究[J].国医论坛,1995,1:30.
[4]唐智敏,茹清静,朱起贵.论肝血淤阻与肝纤维化的关系[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1996,2(3):14.
[5]沈吉云,燕忠生,赵淑媛.肝病血淤证与肝功能肝纤维化标志物的关系[J].辽宁中医杂志,1997,24(6):243.
篇(2)
书法,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瑰宝,也是世界艺术之林中独放异彩的奇葩。这是因为:书法所写的是汉字;汉字是书法的表现对象和造型基础,是书法的生命之源。
一、从书法的内涵看,书法艺术是汉语言文化的应有之义
世界上所有开化的民族都有他们自创的文字,或参照其他民族文字创造的文字,有文字的书写,只是他们的书写都未能成为艺术形式(如拉丁文字、阿拉伯文字等)。此外,现今的汉语拼音字母,是借拉丁文字母创造的,以拉丁文书写方式拼写,人们也不能以书法的素养书写它以取得类似汉字书法的审美效果。这表明:只有汉字才是书法艺术形象创造的基础,书法艺术是汉语言文化的应有之义。
(一)书法的定义,就是特指汉字的书写。
中国书法,博大精深。关于书法的定义(内涵),至今有多种提法,尚未定论,但每种提法却与汉语言文化息息相关。在此,略举几例加以说明:其一,书法,顾名思义,就是书写汉字的方法。其二,书法,是关于汉字书写研究的一门学问。其三,书法,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背景,以“文房四宝”为工具,通过书写汉字来抒情达意的一门艺术。它主要包括笔法、字法、章法、墨法等内容。上述三种提法均表明:书法是以汉字为基础,用毛笔书写的,具有汉语言文化特征的抽象符号艺术,汉字是书法艺术的表现形式。
(二)书法是汉字的艺术表现。
汉字能成为艺术,主要有以下三点原因:一是汉字有一个为别的文字不具有的特点。汉字既不是模拟自然的图画,也不是任何人随心所欲的抽象符号,它是“本乎天地之心,得乎自然之理”,而以象形、会意诸法创作的造型,是根据汉语的单音单词构成一个个具有独立完整意义的形体。二是汉字的形体构成充分体现了人们感悟自然万物形体构成之理。人们在自然千姿百态痕迹的启发下,创造了象形文字。有了象形文字作基础,再造其他的字就有了参照,因此,以会意、形声等造出的字就随语言的实际发展起来。这样,据单音语言创造的具有形体整体性的文字,为以书法创造出具有生命活力的形象准备了很好的基础。三是能使汉字成为艺术的关键是书写。随着实际需要的发展,书写工具的改进,书写技术方法的总结,汉字发展形成了如大小篆、古今隶、章今草乃至楷书、行书体。体势变了,笔画变了,写法变了,但充分运用书段,借汉字的基本结构,创造出具有生动的抽象形式,具备力的运动节律,具有生命机体意味的笔画,营构有生命的形象,这些始终保持着,而且越来越明确,越来越强烈。
二、从书法结构因素看,书法是汉字艺术特质的表现
汉字书写之所以能够成为艺术,除了书写者自身艺术创造力之外,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汉字先天便具有艺术的特质。书法是汉字艺术特质的表现。
(一)书法的艺术语言是汉字的笔画线条。
书法的艺术语言是汉字的笔画线条,是有着一定的限制和高质量要求的线条,即是书家用手直接写出的,具有生命活力的线条。因为汉字的笔画本身具有艺术素质,有着丰富的表现力,不仅是书法者必须依循的,而且是书法者乐于借助的。一是汉字笔画具有丰富性。丰富的笔画才能构成丰富的形体,蕴涵丰富的内容。汉字有甲骨文、金文、篆、隶、楷、行、草等诸多字体,其笔画也由简到繁,不断丰富。如以法度最为完备的楷书为例,其基本笔画就有点、横、竖、撇、捺、挑、钩、折。而且,每种笔画又有多种形态。二是汉字笔画具有意象性。汉字笔画线条,是人们在长期社会实践中对客观事物外形的一种抽象、概括和描述,同时又是人的创造,带有某种意象性。历代每一书法的笔画中都熔铸有书家的意象。三是汉字笔画具有表情性。汉字丰富多样的笔画,与生俱来便带有丰富微妙的情感。不同笔画的线条,给人以不同的情感感受。一般来说,横线使人感到广阔、宁静;竖线使人感到上腾、挺拔;斜线使人感到危急、惊险;曲线使人感到流动、变化、柔和、轻巧、优美等。
(二)书法的艺术形体结构是通过汉字线条塑造出来的。
书法是造型艺术。艺术的使命在于用感性的艺术形象的形式去显示真实。书法艺术的形象是通过汉字线条塑造出一个个奇妙的结构形体。一是汉字形体的象形性影响和促进了书法的形象塑造。中国汉字是象形的,有象形的基础,就有艺术性。汉字始终沿着表意走,符号中仍有形象,“象”的范围也更广了,称之为“象物、象事、象意、象声”。这“四象”属于象形精神,是汉字艺术性的集中体现。二是汉字形体的多样性影响和促进了书法的形象塑造。汉字丰富的笔画和复杂的结构形体,源于自然和表意的特点。书家个人可根据自己的理解和审美追求去创造书法的艺术形象,但无论如何,汉字形体的固有特点是不能忽视的。
三、从发展书法艺术看,必须坚持书写汉字的传统
继承是创新的基础,创新是继承的目的。历代书法的创变规律,都源于特定历史时期对艺术审美的与时俱进,也由于汉字的象形结构渊源,使其中艺术创作有了极大的可塑性和创造性。
(一)书写汉字是书法自身的规定性。
书法汉字包括两个最基本的方面:一是书写性,即书法是书写出来的,不是画出来的,也不是制作出来的,其创作过程是书写的过程。二是书写的对象是汉字而不是其他东西。两个方面是连在一起不可分割的整体。
(二)书法艺术是最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艺术。
篇(3)
企业的伦理文化是一个企业的文化标志,是企业员工的道德约束和道德基础。企业伦理作为一个企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不是外界强加的,是自有企业那一日开始,企业的伦理文化就已深深植根于于企业的发展之中。
一、企业伦理文化与企业管理关系的历史渊源
企业的伦理文化属于文化范畴,是一种较为抽象东西,人们不易察觉。一个企业的管理方式体现了企业的伦理文化,企业的伦理文化也影响着企业的管理方式,两者相互促进。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企业伦理文化。以我国为例,早期企业的管理方式是采用师傅带徒弟的传统方式,伦理文化大都体现在师徒关系上,这种管理模式有好处也有弊端,师徒关系会加深企业伦理文化中的人文情怀,但也不利于企业生产率的提高,现在很多地方小企业依然沿用这种方式。进入现代社会以后,人们的社会生活进入信息时代,很多现代企业采用数字化的生产模式,企业之间若想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脱颖而出,竞争点就必须集中在人才质量的比拼上,人才的竞争使得企业的伦理文化也已经变成激情、竞争、团结和拼搏,企业的管理方式也变的更为精进、更有效率。一方面,将良好的企业的伦理文化赋予管理方式之中,可以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对于企业提高生产力和产品开发率都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良好的管理方式也会反过来作用于企业伦理文化的升华提高,维系职工与职工之间,职工与领导者之间的良好关系,推动企业发展。
二、企业伦理文化对企业管理的重要性
(一)企业的伦理文化是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纵观世界上的百年企业,对其企业文化进行深度探索,我们都会发现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拥有深厚的企业伦理文化,这种企业伦理文化是以道德规范为准则,以社会行为为准则,并且将企业家的管理理念和成功经验进行有机结合,从而形成企业自身的伦理文化,企业的伦理文化包含了企业的价值观,包含了企业自身的行为准则,包含了其独特的经营理念。正是这些企业伦理文化让企业在长期的市场竞争下保持了自身的特点,并且不断发展壮大。可见,企业伦理文化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在企业的管理过程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好的企业伦理文化所达到的目的,不外乎就是使员工将自己的命运与企业联系在一起,使员工关心企业的未来和发展,这也是企业提高生产率的关键所在。成功的企业伦理文化体现在企业对整体战略的设计之上,不是局限在管理的制度上,企业的组织结构上,而是体现在企业的管理风格上。在企业经济发展的过程之中,精神文化往往比金钱和资本占有更重要的地位。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文化中不难看出,企业伦理文化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占据着重要的作用。古代的企业管理者将企业文化当成一种企业理念,在管理过程中对企业文化的充分利用凸显管理者的管理智慧,并且使得企业飞速发展。近代以来,中国的市场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企业文化对企业的发展规划目标与企业的利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提升企业管理的效率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企业伦理文化是企业的源泉
积极地企业文化可以给企业不断注入新鲜血液,使得企业保持生机和活力。当今社会,企业的发展速度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竞争严酷。我们说企业文化有普遍性也有特殊性,家家企业都有自己的企业伦理文化,这是普遍现象,但是企业伦理文化业带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家家企业都有但是家家企业又都各不相同。正是这种特殊的企业文化决定了企业的发展前途与命脉。从某一程度上可以说,企业伦理文化的发展映射出企业的未来,承载着企业文化,有力地保障了企业的管理效率和效益。企业的伦理文化波及范围广大,包含了各部分之间的矛盾关系,其中最最直接的是企业老板与企业员工之间的关系。自工业革命开始那日,就出现了雇佣者对劳动者的剥削,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获得更多的利益。现如今,如果还是以雇主剥削劳动者的资本主义方式来经营企业的方法断然不可取,雇佣者应当把劳动者看成自己的事业伙伴,企业的管理者与员工一起创业,劳动者应当把雇佣老板看作是自己事业上的领导者,双方共同推动自己的事业发展。中国要发展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和谐经济,自古提倡“以和为贵”,因而劳动者与雇主之间就更加不存在社会等级的差别,他们只是在社会活动中扮演了不同的社会人角色,双方遵循“和”、“合”理念,共同推动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
(三)企业伦理文化可以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
企业的管理者带领企业向前发展,企业伦理文化对企业管理者的管理方式影响也是巨大的。企业管理是在企业文化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企业是否成功,与企业本身特殊的企业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有着良好企业文化的公司必定会有着良好的企业形象,企业伦理文化反映的不仅是企业给外界的外部形象,更是企业内部员工之间的团结一致与员工风貌。好的企业伦理文化可以提高企业管理者的管理水平,让员工尽心为企业服务,创造更多的企业价值,提升企业的产出效率,于无形之中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在学生的教育教学中我们提倡“人本教育”,那么在企业管理中我们更应该“人本管理”,以人为本,更加人性化的管理方式才有可能使企业投入最少但产出最多。
篇(4)
1信管专业的特点和能力要求
1.1信管专业的培养目标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培养的本科学生要具备现代经济学、管理学、计算机科学等专业的理论知识和基本技能,能在国家行政部门、工商企业、金融机构、IT产业和相关科研教学等部门承担信息管理工作和从事信息系统的分析、设计、实施和管理以及电子商务等方面的应用型高级复合型专门人才。
1.2信管专业的特点
信管专业的特点是综合性、实践性和先进性。信管专业的主干课程是管理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经济学。培养复合型人才是本专业最大的特点。目前,管理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经济学学科的交叉不但有利于学生的知识拓展,更重要的是,随着信息社会的来临,相关学科的交叉与拓展已经成为各学科发展的新的生长点,而社会发展的现实,也大量需求相关专业的复合型人才。在教育部学科目录中信管专业隶属于管理科学与工程。本专业在管理方面更加注重以管理的基本原理作指导,大量应用现代信息技术,由于学科就业和应用的多行业性,本专业更应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计算机科学知识无疑在信管专业中处于关键地位。但信管专业毕竟不等同计算机专业,它们在共同的计算机技术的基础上信管专业偏向计算机软件和管理。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信息等同于资本、原材料、人才等方面的资源,借助于经济学基本原理、基本方法,研究如何高效地搜集、处理、传递和利用信息,也是本专业学生必修掌握的。
1.3信管专业的能力要求
信管专业的学生除了应具备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和业务能力外,特别强调应具有查阅文献获取信息,了解本专业相关技术动态,不断提高自己的知识的自学能力,同时,应具备掌握信息管理系统的开发、管理和维护技能、掌握电子商务网站建设及网页制作等实践技能。
2数字化学习及其特点
2.1数字化学习的含义
数字化学习是指通过因特网或其他数字化内容进行学习与教学的活动,它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所提供的、具有全新沟通机制与丰富资源的学习环境,实现一种全新的学习方式;这种学习方式将改变传统教学中教师的作用和师生之间的关系,从而根本改变教学结构和教育本质,它包含三个基本要素:数字化学习环境、数字化学习资源和数字化学习方式。
美国教育技术CEO论坛第4年度报告则明确指出,“21世纪的能力素质”应包括以下5个方面:基本学习技能,信息素养,创新思维能力,人际交往与合作精神,实践能力。数字化学习的目标就是要通过现代信息技术所提供的理想学习环境,实现一种全新的学习方式,彻底改革传统的教学结构与教育本质,从而培养出21世纪所需的创新人才。
2.2数字化学习的特点
数字化学习使课程学习的内容具有先进性。通过数字化的学习环境,教师和学生通过互联网能够充分利用当前国内、国际现实世界中的信息作为教学资源,并融入课程之中,让学生进行讨论和利用。这种以现实和实际应用为基础的学习,有助于学生应用知识加深对现实世界的理解。
数字化学习使课程学习的内容具有多层次性。数字化资源具有高度的多样性和共享性,把数字化资源作为课程内容的补充,相对于课本内容,教师和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能力和兴趣选择不同难度水平的内容进行探索和继续学习。在传统的教学中,教师要做到完全尊重学生的差异,因材施教,不是很容易实现的。而事实上每个学生的原认知程度不同,感兴趣的内容也不尽相同,我们应尊重学生的差异性,给每个学生提供宽松的学习氛围。在数字化学习环境中,学生在自主探索的过程中,网络可以完全尊重学生的差异。学生通过数字化学习可以进一步开阔学生的视野,加深对专业知识的理解,为有能力的同学继续深入学习提供可行的途径。
数字化学习强化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目前,互联网已十分普及,教师和学生都能很方便地在网上获得所需学习的课程内容和学习资源。学生可以不受时空限制,通过电脑使用各种学习平台,获得高质量的相关课程信息,同时,也可以实现信息的任意传送、接收、共享、组织和储存。
数字化学习使课程学习的内容具有可再生性。尤其是网上大量的经过数字化处理的课程,这些课程的学习内容能够激发学生主动地参与到学习过程中,学生不再是被动地接受信息,而是采用新颖熟练的数字化加工方法,进行知识的整合和再创造。数字化学习的可再生性,不仅能激发学生的创造力,而且为学生创造力的发挥提供了展示才华的平台。
3信管专业的能力培养离不开数字化学习
3.1数字化学习可以提高信管专业学生的学习能力
信管专业的综合性、实践性和先进性特点,都要求学生具有很强的自学能力。比如,《信息系统的分析和设计》,课本只是介绍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要想完整做一个信息系统,只看课本是不可能完成的,而在互联网上就有很多网站,教你做具体的信息系统,甚至是网络版的信息系统。再如,《计算机组装与维护》,计算机硬件设备更新很快,学生在学课本的时候课本上的内容就不可能是现实中最新的硬件配置介绍,只有通过互联网才能保证学习内容的先进性和现实性,通过互联网学习计算机维护经验和案例,更是可以利用别人的经验提高自己实践性的好的途径。
3.2数字化学习可以提高信管专业学生的信息能力
信管专业的学生要求能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信息收集、加工、处理、控制和利用。这些能力的学习和实践离不开数字化学习,比如,信息检索,互联网不仅是信息的海洋,更是练习检索实践的开放式平台,在公平开放的互联网面前,信息对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和充分的,但信息能力就会千差万别,信管专业的学生要求比其他专业的学生要有更高的信息能力,互联网不仅有大量的统计数据,也有大量的统计报告,通过学习借鉴,可以快速提高学生的信息加工和处理能力。而真实的数据和报告不仅可以增强学生对社会实际的认识,更可以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3.3数字化学习的形式
协作式学习,是指利用计算机网络及多媒体技术,由多个学习者针对同一学习内容彼此交流与合作,结成若干个协作学习小组,以达到对教学内容更深的理解与掌握的过程。与个别化学习相比,协作学习有利于促进学生认知能力的发展,有利于学生健康情感的形成。和以课程为基础的价值教育是通过科目内容来完成教学不一样,协作式教学则是通过“教学的过程”来实现。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在一天的教学中,当把正常应当讲授的课程内容用协作式学习方法讲授,在讲授理论知识的同时也传授了价值观。协作学习模式有两种形式:一是以协作、互助学习小组身份登录网络,参与协作学习;二是以个体身份登录网络,参与协作式学习。协作式学习,要求为多个学习者提供对同一问题用多种不同观点进行观察比较和分析综合的机会,以便集思广益。这不仅对问题的深化理解和对知识与技能的掌握大有裨益,而且对高级认知能力的发展、合作精神的培养和良好人际关系的形成也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探究性学习,美国国家科学教育标准中对探究的定义是:“探究是多层面的活动,包括观察;提出问题;通过浏览书籍和其他信息资源发现什么是已经知道的结论,制定调查研究计划;根据实验证据对已有的结论作出评价;用工具收集、分析、解释数据;提出解答,解释和预测;以及交流结果。探究要求确定假设,进行批判的和逻辑的思考,并且考虑其他可以替代的解释。”可以看出,探究性学习是学生在学科领域内选取某个问题作为实破点,通过质疑、发现问题;调查研究、分析研讨,解决问题;表达与交流等探究学习活动,获得知识,激趣,以问题为中心,自主收集信息、处理信息和应用信息去解决问题的学习方式。创新能力和信息技能是信管专业学生必需具备的两种重要的能力素质。这两种能力素质的培养需要特定的、有较高要求的教学环境的支持,多媒体的超文本特性与网络特性的结合,正好可以为这两种能力素质的培养营造最理想的环境。互联网是世界上最大的知识库、资源库,它拥有最丰富的信息资源,而且这些知识库和资源库的数据都是按照符合人类联想思维特点的超文本结构组织起来的,因而,特别适合于学生进行基于自主发现、自主探索的探究性学习。这种探究性学习是最能体现网络特性和最有利于信管专业学生能力素质培养的重要教学模式。
篇(5)
一;共同的工具使用;大家都知道,中国书法与绘画的使用工具最基本的都是离不开毛笔、墨水与宣纸。也就是说,写一幅书法或创作一幅中国画作品,都是先用圆锥形的毛笔醮上墨水,然后在宣纸或绢布上用点用线写出画出,只是中国画比书法多了种色彩罢了!所以,如果缺点那三元素就算不上是真正的中国书画(除了极个别在特定的环境所写所画以外,如壁画,碑刻,或其他的......)。当然也许有人会有异议,说某些人画国画写书法并不需要毛笔,而是用排笔或其他工具(如国画以模具印,用水壶喷。书法用布拖,挥扫帚等),其实那只是极个别的人,在追求他们自己心目中认为那所谓的“特技与创新”罢了!根本就不能视为什么正统(当然国画有时脱离毛笔直接用手画,用模具印,用水壶喷,如果是画面局部的需要,而临时采用的特殊方法那倒是许可的)。总则,要知道,中国画理论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讲究“骨法用笔”(这一理论同样能适用在书法创作上)。"骨法"指形体结构,就是以线条为主要表现形式。它是构成点画与形体的支柱。也只有通过那一条条一点点遒劲有弹性的钩线、点戳,来追溯出那种至高的骨力。因为线条是书画艺术的生命力,任何一幅作品中每一根线条的强与弱会直接关系到此幅作品的成功与否,极其重要。而线条的产生就必须能过毛笔勾勒出来。所以说中国书画相同的是;第一绝对离不开毛笔。其次,不能离开宣纸。因为只有在宣纸上写写画画才能产生出那种特殊的艺术韵味。就比如画一张写意国画,如果你不选择渗透力很好的宣纸,而用其他纸张代替,就是功力很高的大师,也不可能表现出想要达到的艺术效果。书法同样道理,如果写楷书时,却选用渗透力极强的生宣纸,就不可能写出理想的字。墨水就更不用说了,因为其本来就是中国书画的血液。所以说无论画画写字,不但离不开那三种工具。还要根据不同的描绘对象,而加以对材料工具的认真选择。
二;共同的用笔用墨技巧;笔墨是中国书画的特色精华、物化载体与精神折射。不同的行笔、和墨色的千变万化会使书画作品变得更有情有趣、有气有韵。如果一幅作品中缺少笔墨,就难言成为传统的中国书画。两者在用笔和章法的错落处理上简直如同出一辙。最基本的也就是同为用线传力度,用形传情感,讲究线条与墨点的连贯性。两者用笔方法同为依靠手腕和手臂来控制行笔的速度,都是通过笔的中锋、侧锋、顺锋、藏锋、露锋、逆锋相互转换,与提、按、顿、挫、疾、徐等虚实变换的有机结合,并着重于手、眼、心三者之间的相互协调配合,才能让笔下的线条有骨有肉、有质有韵、险劲率约、刚柔相济,产生出较强的形式美、拙重美、厚度感与节奏感。就如唐代韩方明《授笔要说》中提到:“执笔在乎便稳,用笔在乎轻健,轻则须沉,便则须涩,谓藏锋也,不涩则险劲之状,无由而生;太流则浮滑,浮滑则俗”。
在用墨方面,也许有人对书画的相同会持有异议。他们认为在国画中墨色运用非常讲究“墨分五色”,通过那焦、浓、重、淡、清之间的相互转换与结合,干湿明暗对比来达到画面中骨肉相益,血脉相通,但书法就非也。他们认为书法作品墨色基本单一,整幅作品只有黑、白两种全概括。也就不需要什么黑色变化之说,其实,此看法差矣!一幅成功的书法作品,不仅仅看线条、结体、章法,墨的浓淡、干湿、重轻是同等重要。墨的运用,可以说就是一个书家生命节律的折射。作品中如墨过湿,干后灰平,写出的字有肉无骨。反之,墨过浓过干,笔下的字则有骨无肉。欧阳询《八法》中曾说过“墨淡则伤神彩,绝浓必滞锋毫,肥则为钝,瘦则露骨”。字的血与肉就是通过水墨之间的相互调节,如果得当,才能产生“穷变态于毫端,合情调于纸上”的理想效果。当然墨与水相互调和时要先考虑到书写的毛笔的大小、字的风格,字体、尺幅、与宣纸的渗透力强与弱等等,用墨浓淡一定要掌握一个“度”,并不是那么随意性。所以墨的浓、淡、润、燥、等等在书法创作中是一样极其有讲究的。要达到那精、气、神、骨、肉、血六点齐,方称完美。缺一而不成书也。
三;共同的审美与意境追求;书画艺术的审美是属于意识思维中的高级层面。二者虽同源、同作为视觉艺术又是属于两个不同的类型,在漫漫历史长河的嬗变中,是以遵循着一个共同循则,同气连根,互动互通、又是独立性来发展。书画艺术的审美价值都蕴含在作品的意境里。强调“以形写神,以形写意”(当然绘画的形是具象,而书法是抽象),用形意抒情来表现人生,来对生活的高度概括、提炼和升华。比如,我们在欣赏一幅书法或绘画作品,首先并不是看局部,而是先观其整体、画面的起承开合、气势脉络,然后注意笔法、再观察字的结体或画的层次。书法里面的一笔一划,国画里面的一点一块,都讲究形、意、神。同是通过笔墨的表达,来创造出有筋骨血肉、有强烈生命活力的艺术风格形象。追求那种气势、韵律、节奏、的结合,达到艺术的最高境界,真、善、美!当然一个人的生活环境、学识、修养、个性和笔墨功力运作的高低,能直接反映出作品所表露出情感意境的粗浅、深厚、单调、丰富。还有,在一幅真正完美的书画艺术作品中,里面的一笔一点是不可能偶然出现的、都是书画家的苦心经营,让各点线紧密衔接,达到“遗貌传神”。如一幅行草书作品,我们要是单单看里面的某一个字,或许会觉得写很败笔。或字体变形、或多笔少画、或重心倾斜,让观者感觉摇摇欲坠,极不顺眼。但,如果同时留意上下左右相邻的字,整体来欣赏时你或许会为书家那绝妙的章法布局而叫绝。举例;一个字的重心向左下方倾斜,而下面一个字的左边偏傍书家故意往上提,起到补救与稳定上字重心的不稳(就好比如一车子轮胎爆了,车子倾斜,就得先用千斤顶将其托起,让车子停稳)。这是让作品在险中求稳,在变化中求统一,达到气势连贯和完整,构成了艺术之美感。书法艺术往往就是在履行实用的同时,在那方寸的点划间,体现出书家本人的思想寄托与文化取向。都是表现在笔墨,落实在人文精神中。
篇(6)
1会计电算化与企业信息管理的关系
会计是经济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企业的会计信息约占企业全部信息的70%,会计电算化系统在企业信息管理系统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如果把管理信息系统比作大脑,那么会计电算化系统就好比神经中枢系统,控制着整个系统的运行。会计电算化是整个企业信息化的重要保证。
会计电算化是采用电子计算机替代手工记账、算账、报账及对会计资料进行电子化分析和综合利用的现代记账手段,是以电子计算机为主的当代电子和信息技术应用于会计工作中的简称。企业通过实现会计电算化,使财务人员从繁重的手工操作中解脱出来,从简单的核算向企业的经营管理和决策的方向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企业信息管理的核心是企业资源计划(ERP),它以供应链管理(SCM)为重点,以财务成本控制为目标,通过精心设计的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把从原材料开始到产品服务整个过程企业所拥有的人、财、物、信息、时间、空间等资源进行综合平衡和优化管理。
如果一个企业真正建立起信息管理平台,那么基于模拟人工业务内容和流程,与实时发生业务处理、管理控制相分割的传统会计电算化,无论是从技术上,还是内容上都将发生一次质的飞跃。其意义将不亚于从手工会计系统到会计电算化系统的飞跃。那么,建立在企业信息管理化下的崭新的会计电算化———“会计化系统”将是一个基于互联网的信息系统(传统的会计电算化是基于局域网的信息系统),是一个能与业务协同处理,能实时进行数据处理,实时管理控制的系统,是一个信息高度集成和共享的系统。它能随时查看各种成本费用的实际发生情况,变事后反映为事前分析,事中控制,随时利用账表一体化产生业务执行数据,为领导正确决策提供准确、真实、可靠的数据。
会计电算化与企业信息管理系统相融合,改变了传统的单一信息生成和传递结构,进一步加强了财务职能与企业各环节的密切联系。使企业的信息资源达到最佳配置。
2企业信息化管理对现行会计电算化的影响
2.1对会计数据输入形式的影响。在企业信息化环境下,会计数据的输入形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是书面形式的原始凭证在很多情况下被电子数据所代替,如电子商务产生的交易凭证、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自动记录的生产数据等。二是原始凭证的输入点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在财会部门,而在产生数据的业务部门,如采购部门、销售部门以及办公自动化环境中。三是大多数记账凭证将由会计电算化系统自动产生。会计数据输入形式的改变将对传统会计岗位的设置、数据处理流程、会计数据资料的生成与管理带来一系列的变革。
2.2对会计数据处理内容的影响。传统会计数据的处理围绕会计要素展开,会计信息主要是价值信息,最后形成若干通用会计报表传递给信息使用者。会计的主要目的是确定资本价值和最佳收益,信息使用者通过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等数据就可决定决策模式。这种会计方法的特点是,提供的会计信息对所有不同信息使用者都是统一的、事先确定的、综合性的、单一计量的。在企业信息化环境下,数据库信息为整个企业信息系统共享,它存放的是企业最基本的经济活动事项的数据,而不是按会计要素进行货币计量并分类、归并和综合化的数据。利用数据库技术、网络技术和计算机极强的数据处理能力,使会计信息化系统在企业管理信息系统中的综合系统地位得到加强,由原来的以提供日常核算资料为主,发展到对企业的各类管理人员提供信息。另外,基于互联网的会计信息化系统的发展,大大扩展了会计数据处理的时空范围,远程处理、使实时监控成为可能。
2.3对数据处理流程的影响。在企业信息化环境下,数据处理流程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是数据处理流程的起点由财会部门的凭证输入点扩展至企业的业务源头,进入系统的业务数据的准确性直接关系到系统数据处理的准确与否。二是日常的会计数据处理和信息输出均由计算机网络系统自动进行,除非出现计算机安全问题,计算机内部数据处理一般是不会出差错的。也就是说,只要保证输入的正确性,一般也就保证了处理和输出的正确性。因此,在计算机内部没有必要模仿手工处理流程进行账账核对和试算平衡处理,数据处理流程可直接根据实际的数据流来设计。
2.4对会计数据生成与管理的影响。企业信息化以后,会计数据的生成与管理将会发生很大变化。一是由于集成系统处理总是以最基本的交易事项为处理单元的,因此记账凭证的数量将会大量地增加,再打印记账凭证将会付出较高代价。二是书面形式的原始凭证或不存在,或分散在企业的业务源头,再强调记账凭证与原始凭证的书面匹配,将会人为增加冗余的业务流程和处理工作量。三是随着社会信息化的发展,会计信息的查询、使用以及财务报表的越来越趋向于网上在线的形式,因此在信息化环境下,基于书面资料的会计数据生成与管理办法应过渡到基于电子数据的会计数据生成和管理办法。
2.5对会计数据处理组织的影响。传统会计组织结合内部控制的要求按会计工作的不同内容进行划分,并相应地配备会计人员开展数据处理工作。在会计电算化系统中,原先由会计人员分工完成的许多内容都由计算机集中自动地完成,因此组织形式和人员配备必然会发生较大变化。尤其是当企业信息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和规模时,会计信息化系统将完全融合于整个企业信息系统中,企业内部传统的部门界线、数据处理职能分隔将越来越模糊。
3实现会计电算化与企业管理一体化存在的问题
3.1运用了电算化系统的企业,只是解决了会计核算与财务管理方面的问题,尚未进一步提出全面的企业信息管理一揽子解决方案,因此无法实施会计核算与信息管理网络资源共享。许多企业既上会计电算化,也搞信息网络平台,但从一开始两者就是分离的,不相干的,缺乏统一和长远的规划。
3.2不同所有制企业和不同行业所运用的电算化软件版本种类多样化,系统开发与应用平台不相兼容,系统结构复杂化。为数不少的企业所运用的电算化系统大多是软件单机版,跟企业的信息管理一体化往往是脱节的。一些企业实行了核算的网络化管理,但没有与整个管理平台连接起来;从而为信息一体化的推进增加了难度。
3.3安全性问题是顺利实施网络会计的重要因素,在网络化迅速发展的今天,垃圾文件泛滥成灾,网络黑客充斥其间的时代。安全性问题已经成为网络会计发展的生死攸关的问题。会计信息是反映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重要依据,不得随意泄露、破坏和遗失。在网络环境下,大量的会计信息通过开放色INTERNET传递,置身于开放的网络中,存在被截取、篡改、泄露机密等安全问题,很难保证其真实性与完整性。
3.4会计电算化与企业信息管理系统相融合,对相应会计人员的素质要求也较高,要求会计人员既懂会计、又懂管理,不仅熟悉会计电算化知识、又熟悉网络知识,既会会计业务操作,又能解决实际工作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但目前相当一部分会计人员不能适应这种发展的要求,因此人才问题成为网络会计发展的一大问题。
实现会计电算化与信息管理系统的统一,必将为企业今后的飞速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篇(7)
企业文化与企业管理分属于不同的概念,其内在含义存在差异,但均属于企业发展的重要资源,且两者间存在密切联系。实践证明,企业文化和企业管理的高效融合是推动企业长足发展的内在动力,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保障。因此,企业必须重视企业文化与企业管理的关系,采用有效手段,达到企业文化与企业管理的高效融合,推动企业发展。
一、企业文化基本概述
企业文化的含义存在狭义与广义之分,广义上的企业文化,指基于人类社会发展实践作用下,创造出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狭义上的企业文化,指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逐渐产生的具有企业特色、被企业职工所认同的精神、价值观和经营理念。本文所研究的企业文化,属于企业文化的狭义层面。对于企业文化,其蕴含的价值观和经营理念对企业员工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具有引导和促进企业员工树立与企业文化相符的价值观、人生观的作用。换言之,企业拥有何种价值观和经营理念,则会培养出具有相同特征的企业员工。总之,企业的价值观、经营理念、企业精神以及企业制度是企业文化的基本内涵,是企业文化的重要体现。
针对企业文化,其具有以下两个特点。第一,时代性,国家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企业发展环境在变化。因此,为适应不同经济时代的不同发展需求,企业需不断转变发展方式与方法。基于此,企业文化是企业发展的重要体现,是推动企业发展的有效动力,为满足企业发展需要求,企业文化需具有时代性。第二,个性化,企业文化是企业形象的象征,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体现。不同的企业,具有不同的特点,因此,企业在建设企业文化时,应以企业发展特点为依据,结合时代特征,建设具有个性化的企业文化。
二、企业管理基本概述
企业管理,指企业管理层对整个企业的经营管理行为,基于企业管理作用下,制定企业整体战略发展目标,进行生产组织、领导工作的安排,有助于实现企业经济效益最大化,推动企业发展,有利于增加社会效益,满足人们对不同产品的不同需求。企业管理直接关系着企业的生存发展,是影响企业经营的关键因素,与企业的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存在直接联系。与此同时,企业员工价值观的形成与企业管理存在密切联系。简言之,企业管理的效率是企业经济利益的决定因素,因此,企业管理者应充分认识到企业管理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优化企业管理模式,采用先进管理理念,为企业长足发展奠定基础。
三、企业文化与企业管理的相互关系
一方面,以整体视角为出发点,社会经济组织是企业的存在形式,文化的形成、发展与企业的经营管理存在密切关系。企业文化渗透至企业管理的每一环节,服务于企业管理是企业文化建设和发展的宗旨。企业文化与企业管理具有相同的服务对象,而企业员工是企业管理与企业文化活动的中心点。企业文化作为企业发展的灵魂,其与企业管理相一致,贯穿于企业生产的每一环节,且以实现企业经济效益最大化和社会效益最大化为最终目标。
另一方面,企业管理与企业文化具有共同作用、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相辅相成的关系。企业管理与企业文化的作用存在相同点,其调控、约束、规范以及引导是两者的基本功能。两者所追求的最终目的具有一致性,即提升企业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推动企业发展,引导企业员工搭建与企业发展战略相一致的愿景,从而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充分发挥自身价值,推动企业发展。由于企业文化与企业管理存在相同的目标、服务对象,致使两者必须结合。基于现代企业经营,企业文化融入至企业管理中成为诸多企业发展的重要手段。因此,企业管理者,在建设企业文化和企业管理过程中,应正视两者间的密切关系,充分利用两者的内在联系,为企业实现整体发展目标奠定基础,保证企业在激烈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
针对企业文化,其对企业管理具有促进作用,具体表现在企业文化的凝聚作用、指导性作用、约束作用以及激励作用。具体而言:
第一,凝聚作用。企业文化是企业精神的核心,是影响企业工作氛围和风气的关键因素。企业文化在制定具体目标的基础上,指导企业员工树立相同的奋斗目标,将企业员工紧密联系起来,发挥其凝聚作用,为企业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基于此,企业向心力得到提升,大大提高企业员工工作效率,为企业管理提供便利。
第二,指导作用。企业发展以企业文化为核心,是企业成员智慧和经验的浓缩,具有指导企业发展目标和发展方向的作用。利用企业文化对企业发展的战略性指导作用,准确预测和规划企业发展趋势,迫使企业管理思路更加清晰、明了,为企业决策提供可靠依据,实现企业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目标。
第三,约束作用。企业文化是基于企业内部自觉作用下,形成的行为意识规范,是企业文化约束力的体现。通过企业文化,规范企业员工的思想和行为,提高企业管理效率,强化规章制度的执行力。不同特色的企业文化,对企业员工素质的工作态度存在不同要求,这需企业管理借助企业文化的约束作用,引导企业员工树立正确的思想意识,达到提升企业管理执行力的目的。
第四,激励作用。企业文化是先进工作思想与态度的体现,具有人文性强的特点,其将企业员工的个人修养和工作态度视为重点。企业文化利用精神力量,指导员工形成正确的思想价值观和工作态度,迫使企业员工重视自身价值的实现,致使企业员工秉承着积极向上的工作态度投入到工作中去,从而在工作中赢得使命感和荣誉感,实现自我价值。
四、实现企业文化与企业管理有机融合的途径
(一)企业文化坚持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
为保证企业文化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企业应不断提升企业内部管理能力,以建设企业思想为基础,坚持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增加企业员工在企业中的归属感,提升企业员工整体凝聚力,达到激发员工工作积极性的目的。基于以人为本基本理念的企业文化背景下,企业员工拥有共同的目标,且为实现目标不懈努力,推动企业生产经营能力发展,实现企业经济效益最大化,增加社会效益,促进企业发展。
(二)强化企业制度建设
企业文化建设并非一朝一夕,其需在实践基础上,不断完善、优化。因此,企业必须强化制度建设,充分发挥制度的约束作用与指导作用,为企业文化建设提供保障,迫使企业文化建设得到规范。与此同时,在企业制度建设基础上,消除企业文化中的不良影响,引导企业员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为企业发展贡献自我力量。针对企业成文的刚性制度,其约束力较强,有助于规范企业员工行为,指导企业员工正确认识企业文化,掌握企业文化的作用与价值,体会到企业文化在企业发展中的重要性,进而接受并认可企业文化,为企业文化和企业管理的有机融合奠定基础。
(三)增加企业员工对企业文化的认识程度
为保证企业文化深入人心,企业应定期或不定期的开展不同类型的活动,达到增加企业员工对企业文化认识程度的目的,促进企业文化与企业管理的高效融合。例如,定期向企业员工征集符合企业文化的标语,为企业员工深层次理解、分析企业文化创造条件,若发现企业员工对企业文化存在误解时,应及时进行纠正。通过企业文化宣讲,帮助企业员工深入学习企业文化,引导企业员工通过企业文化约束自身行为,为自身发展创造有利条件,达到提升企业内部管理水平的目的。以企业文化为媒介,构建完善的奖惩制度。通过奖惩制度,激发企业员工主动、自觉的学习企业文化,掌握企业文化内涵,探究企业文化建设途径,为企业文化建设提供保障。
(四)完善企业核心价值
篇(8)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包装已由商品的附属地位逐步演变成为商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重视商品的第一质量的同时,千万不可忽视了商品的第二质量既商品的包装设计。包装的质量不但直接影响着顾客的购买欲,更重要的是会影响商品的品质,严重的话甚至会影响到国家的声誉。由于历史原因,中国的包装业起步晚,需要理顺的环节多;需要修正的观念多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大,这是中国包装的现状。在这种背景下,借鉴国外成熟的理念和先进的技术是行之有效的方法。然而,一味地将中国包装的希望完全寄于"洋"。则不符合实际,可能会导致"水土不服""消化不良"等负面效果,反而会使中国包装误入歧途,因为优秀的传统文化是维系一个民族的生命线。我国是一个有着六七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具有既厚且广,博大精深的优秀民族文化底蕴,这一切都是我们后人享用不尽的宝藏,我们只有很好的继承和发扬中国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同时吸收国外成熟的经验与先进的技术,才能使我国的包装设计立于世界包装之林。
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风格习惯、文化教育、历史传统、道德、人生观、价值观的融合。而包装设计中的民族特色则是民族文化在商品包装上及商品中的形象化、特征化、具有代表性,能够在文化心理上接近消费者,与消费者紧密沟通,这是包装设计富有成效的一个重要且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因此,更深层次地去挖掘中国文化艺术中的宝贵财富,对中国古代以及民间的艺术和设计进行深入的学习和创新,才能使中国的民族文化更好的借助包装这一宣传媒介传播于世。然而,在当前,有一些短视的设计师被大量的西方设计观念和作品蒙蔽了双眼,在"西风"的声浪中迷失了方向。只是一味的推崇西方设计流派,设计大师。而对中国的传统优秀文化漠不关心,全盘否定,或是追求设计形式上的哗众取宠,却对生活失去了真挚的理解。生活是设计的源泉。没有生活,便没有设计艺术。这一真理永远具有意义。注重生活,消化和吸收中外优秀文化的精髓,发展自身的竞争力以抵制西方国家的经济侵略,这是我们当前设计师不可推卸的历史职责。
当今世界,象中华民族这样的一脉相传的国家屈指可数。基于这一点,中国人对于传统文化情有独钟。回顾历史长河,曾经盛极一时的古埃及文化,在经历过古王国、中王国和新王国的辉煌之后,终于在公元前11世纪沉寂在尼罗河腹地的沙漠深处;曾经为地中海点燃文明之火的古希腊文化,在经历过克里特-迈锡尼文化的辉煌、希腊城邦的繁荣、亚历山大帝国的东西方交流之后,终于在公元前2世纪的三次马其顿战争之后,折戟沉沙在爱琴海中;建立在古希腊文化基础之上,把古希腊文化发扬光大的古罗马文化,在辉煌了上千年,完成了地中海文明的传承任务后,也在蛮族的劫掠下,于公元5世纪退出了历史舞台。而中国的民族文化却保持着丝丝入扣的传承关系。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之下,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中华民族的子孙,都以传承和发展中华文化为己任,为荣耀。这种使命感,不仅为占绝大多数的汉民族所独有,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兄弟民族所共有。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长卷中,真正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儒家,道家和禅宗。儒家创始人孔子以其"仁学思想",深刻地解释了美与善的关系。道家主张"无为",认为美在于超越功利的自然无为,采取听其自然的心态,从而达到"物我合一"。佛教的"禅宗"则崇尚"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的宇宙合一的精神。总之,中国传统文化长期以来坚持从个体到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的灿烂成果如若在包装设计形态中以形象化的直观方式和情感语言表达出来,它定能为中国的包装设计带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但其前提是必须深入地去研究中国传统民族文化的各个方面。认识越深则底气越足,其设计也越有厚度。然而,这里所谓的民族文化的体现并非是简单的在包装上画上一、二个京剧脸谱,或者把塑料换成瓷器。因此,对本民族文化的理解不能只立足于形式,应该切实地把握其精神所在。
下面就笔者就如何将民族传统文化更好地融入包装设计中作一些探讨。一个成功的包装设计必须合理运用并巧妙搭配包装的五大核心要素。即文字、色彩、图案、材料、造型。首先,我国的文字演变也就是文化历史的演变过程。如:在中国的传统书法中,有着不同风格的正楷、草书、隶书、篆书等。这些传统的文字书写形式在现代包装设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每一种字体都曾有过一段辉煌的历史。例如图1笔者以传统书法字体和传统粽叶作为包装设计元素以此体现寿司的悠久历史。
其次,包装的色彩运用对消费者心理有着很大程度的影响。然而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宗教对色彩的要求及认识也不一样。如中华民族对红色有着崇敬和热爱的情意,习惯将红色用于喜庆和节日,它给人以热烈、热情、向上、团圆的色彩感觉,象征吉祥、幸福、威严。例如图2笔者为元祖食品系列所做的包装作品。作品以红色作为基调以及传统年画图案给人浓郁的民俗喜庆感。但是在西欧,一些国家却对红色有仇恨和恐惧的心理。在他们心理上认为红色有粗暴、侵略和战争的色彩感觉。因此,在选择包装色彩时要严格考虑消费者的差别,研究和掌握不同消费者对色彩的不同心理接受程度。要投其所好,因人而异,就应该首先了解当地的传统文化和习俗。
再次,图案是包装设计中的重中之重,传统图案在包装中广泛应用。既美化了商品的外观又体现了独特的民族精神。自古以来,有关的传统可视图形。如:雕刻、剪纸、刺绣等工艺品图案,以及诸如戏剧、服饰、脸谱与道具、兵器、建筑、家具、生活用品、纺织印染等物品的装饰图案纹样,还有古典名著、民间传统、神话故事等作品中内容场景的插图等等。例如图3笔者所做"中国文明"丛书的书籍装帧设计采用了大量的中国传统图案来传达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这些传统图案只要与被包装的内容物有较密切的有机联系,而且运用合理得当即可很好地体现现代设计中的传统文化的因素。但是在图案的运用中更应关注不同国家、民族和地区的不同审美观念,以免犯了某些地区消费者的忌讳而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总之,了解各个民族和地方的不同审美观念以及特色文化产品,对于包装的成功设计和打通产品的销路无疑是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无锡的泥人工艺品、油面筋及酱汁排骨等食品;苏州的松子糖、卤汁豆腐干食品、苏绣、檀香扇工艺品等;宜兴的紫砂茶具、南京的盐水鸭、板鸭等;安徽省的宣纸与墨、砚等;山东省潍坊的风筝;上海老城隍庙五香豆、梨膏糖等等。如图4中笔者为老城隍庙系列食品所做的包装设计。作品以上海滩老月份牌为基调配以多种传统装饰手法来表现城隍庙系列食品的地方传统文化。这类产品在包装设计中一定要将现代先进包装技术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神韵两者相交融,这样才能使包装在增加商品价值,增加商品竞争力,提高企业的知名度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生活意识形态的提高,还可充分反映中国的湖光山色,风土民情,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对外宣传中国的形象,促进中国旅游业的发展和民族文化精神的展现。最后,包装的材料运用,以及包装的结构与造型也是包装设计中不可缺少的元素。传统包装材料主要是利用自然界的天然物品。如竹子,我国是世界上有名的竹乡、民间编制竹制品的种类很多,可以用来包装的就有托篮、竹盒、竹筐、竹篓等,而且能编制出许多生动、漂亮的图案,若我们巧妙的加以利用,就可开发出不少新颖别致的竹制包装。值得我们利用的不只是竹子,还有木、藤、贝壳、葫芦、粽叶、芦苇叶、等天然材料也可设计制作出具有反璞归真的意境。例如图5笔者为俏妮诗巧克力所做的包装设计。作品以木材作为其包装材料来体现天然食品的淳朴性。在包装造型与结构上可以借鉴传统的建筑、交通工具、家具、生活用品、娱乐用品、文具用品、体育用品、宗教用品等等用品生动、漂亮的图案,若我们巧妙的加以利用,就可开发出不少新颖别致的竹制包装。值得我们利用的不只是竹子,还有木、藤、贝壳、葫芦、粽叶、芦苇叶、等天然材料也可设计制作出具有反璞归真的意境。例如图5笔者为俏妮诗巧克力所做的包装设计。作品以木材作为其包装材料来体现天然食品的淳朴性。在包装造型与结构上可以借鉴传统的建筑、交通工具、家具、生活用品、娱乐用品、文具用品、体育用品、宗教用品等等用品中具有艺术价值和欣赏价值、且较为符合被包装对象或与被包装对象有着较为密切联系的要素特征。设计中应注意造型的美观、别致、精巧、结构的科学性和牢固度。纵观世界各国对于包装设计中民族文化的表现都与各国哲学、历史、经济背景相连。英国的包装设计受其严谨的正统文化影响,风格较为华贵具有古典、优雅气息。德国的包装设计受其哲学思想方式的影响,富于理性的传统特征。法国的包装设计呈现着一种融设计与艺术精神于一体的浪漫特色。而日本包装设计面对经济的高速发展,融会了大量的日本传统视觉因素,又体现了时代感,并形成了独特的日本风格。就是因为这些国家吸收了外来文化的同时,更加强烈的意识到弘扬民族文化的重要性,使其本土文化与现代设计得以交融。在此要特别说明日本的包装设计。同样在东方大文化背景的影响下,日本的包装设计既有强烈的时代特征,又蕴涵深遂的东方民族文化精神,有更多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地方。近几年来,随着我国设计师对传统文化的日益重视,也涌现出不少优秀的包装设计作品。不难发现,一些成功之作之所以成功,往往是恰到好处的运用了传统文化的精髓。这些作品既能体现出包装设计的时尚性,又能折射出各地区、各民族的不同的历史、文化特征和审美方向。例如:北京理想设计公司的"申奥标志设计"(图6)也有独到之处。申办会徽由奥运五环色构成,形似中国传统民间工艺品的"中国结",又似一个打太极拳的人形。图案如行云流水,和谐生动,充满运动感,象征世界人民团结、协作、交流、发展,携手共创新世纪;表达奥林匹克更快、更高、更强的体育精神。香港现代设计大师靳埭强先生的设计作品运用水墨语言结合现代设计技巧为中国的平面包装设计领域开拓了新境界(图7)。
基于以上的阐述,传统文化是人类历史文化长期发展过程中的积淀。研究传统文化是为了更好的将他们运用于现在和未来。社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这种时代的责任感与紧迫感使我们每一位从事设计的人员不得不思考:如何将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融汇贯通,相辅相承去开拓新的历史空间。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的包装设计领域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需要更多的理性思维,更强烈的民族责任感,这将促使我们不断创造、完善一个全新的民族设计体系。
参考文献:
篇(9)
一、在演示实验中培养学生观察能力,提高学生实验素质
化学教材上的每一个实验,都是在化学基本概念、基础理论的前提下,安排得恰到好处。作为一名化学教师,必须深入钻研实验教材,吃透实验目的,把握实验实质,使每一个学生观察实验现象后,素质有所提高。
1.1演示实验要精心准备,做到细微周到
化学演示实验是培养学生观察能力的有效途径。每一个演示实验,都会潜移默化,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准备好演示实验,是化学教师备好课的重要组成部分。教师应先到实验室,同实验员一起认真准备,同时虚心听取实验员的意见及建议。从仪器、药品到实验装置、实验操作,都要考虑得细微周到,点滴不漏。对实验中可能出现的不利因素和反常现象,要心中有数,课前排除。实验前,要认真预做一遍乃至多遍。从实验物品的摆放艺术、实验装置的安装顺序、操作规范程序都要身临其境。只有这样,才能把握演示实验,提高学生观察能力。
1.2演示实验操作要规范化,行为要准确化
课堂上演示实验要规范化。每一个实验,所用的仪器药品,在讲台上摆放要整齐有序,给学生美观大方的印象,培养学生的审美观。切忌满台仪器药品,杂乱无章。做实验时,教师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要严谨认真,规范准确。从药品的使用,仪器的安装,气体的制备及检验,要环环紧扣,顺理成章。每一个细微动作,都要做好。教师的每一个动作尽在学生的观察之中,对学生的观察能力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通过教师的演示实验,使学生对化学实验产生一种新鲜感、美观感,使他们在心灵深处产生一种新的求知欲。同时,为以后的学生实验奠定良好的基础。如金属钠和水反应产生氢气的实验,教师要先剪好铝箔,穿好针孔;再切好钠块,包好钠块;试管要预先装满水倒立在水中,然后提起试管靠近水面,将包有钠块的铝箔放在试管口下,收集氢气。尔后用拇指赌住试管口,提出水面,做验证实验。整个实验要熟练有序,轻车熟路,使学生看后,受益匪浅,观察能力得到较大的提高。
1.3演示实验要多采用启发式,启迪学生创造性思维
演示实验不能只局限于课本实验,要结合实验内容,扩展实验的外延,启迪学生积极思维,使其通过实验观察——信息输入——思维分析,获取实验新知识,提高化学素质。
每个演示实验无须从头至尾由教师全部做完。也可开始设置疑点,创设实验情境,采用点拨提问法、师生共做法、学生演示法,促使学生积极观察、思维。提问也应分类型,多提问不同类型的学生,使不同类型学生的个性思维都得到发展。如铜和浓硫酸反应,让学生先预习实验、提出问题。很快优等生提出SO2有毒、污染环境,有害同学健康,不能排放教室。同时,提出改进意见,变开口式实验为密封式实验。中等生提出了该反应的反应过程及机理,并指出反应后颜色的变化。差等生实验后通过观察颜色变化,搞清了反应过程。整个实验气氛热烈。此时教师要因势利导,多做点拨,让学生举一反三。教师要深深懂得,采用启发式演示实验,往往会收到事半功倍之效果。同时要捕捉学生实验中的闪光点,一旦发现,及时诱导,使整个实验氛围生气勃勃,充满活力。促进学生个性思维的发展,使学生思维能力得到进一步提高。
二、在学生实验中,培养学生多种思维能力,提高学生创新能力学生实验是培养学生多种思维,提高学生分析能力、创新能力的有效途径,只有抓住这一点,才能有效地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学生实验是根据学生学习的知识点及时安排的,意在通过实验,巩固基本理论、概念,对新学知识产生新的飞跃,增加学生手脑并用能力。因此,做好学生实验,对学生的学习巩固提高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2.1实验前,组织学生认真预习
实验前,要认真组织学生预习,使学生了解实验目的及方法、实验仪器及实验原理。要布置一定的实验预习题,促使学生积极思维,让学生学会看书。通过预习,使学生把要我学自觉地变成我会学、我爱学、我想学。也可以在习题中设置疑点,使学生学有压力,有动力。也可按实验小组,布置不同的实验讨论题,促使学生多角度思维,激发学生求知欲。通过预习,初步解决实验中的一些问题,如实验目的、实验步骤、操作技巧、仪器装置等。
2.2实验课上精讲10分钟,开发学生智能
教师要认真备好实验课。一节实验课,就是培养学生能力,提高学生实验技巧的全过程。有些实验,可培养学生多种思维的发展,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因此,备好课显得尤为重要。实验教学要细致认真,开拓创新。既要完成实验内容,又要兼顾程度不同的学生。对有难度的实验,可设法化解实验,降低难度。对优等生,要求对原有实验提出改进意见,变验证性实验为探索性实验。备实验课,最好到实验室,亲自参与实验准备工作,了解实验的全过程。
实验的讲解,要精讲,宜简不宜繁,时间不宜超过10分钟。板书应清楚精炼,写清注意事项及实验改动。让学生在实验课上既有章可循,又不妨智力开发。如酚醛树脂的制取实验,提出两种实验方案:一种以浓Hcl作催化剂;另一种以浓NH3·H2O作催化剂。让不同的实验小组同时做,结果发现树脂颜色截然不同,学生兴趣盎然,教师可因势利导,讲清树脂结构不同,从而解开学生知识上的迷雾。设置疑点对学生来说是一种思维催化剂、兴奋剂。通过实验,可加深学生对基本概念、理论理解的深度,拓宽知识面,达到复习巩固提高之目的。
篇(10)
语言是社会的产物,是人类历史和文化的结晶。它凝聚着一个民族世代相传的社会意识,历史文化,风俗习惯等人类社会所有的特征。不同的文化背影和文化传统,使中西方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生活方式等方面也存在有相当的文化差异。
首先,在文化的定义方面,文化是一个很泛的概念,对它的定义很难。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文化的定义便不相同。Williams (1985)年的定义比较科学,他将文化定义成三个层面,首先,是精神层面,即价值观,道德观和思维方式等;第二个层面是具体的,指历史遗留下来的书面文件,如史书等,这对人们对文化的认识也有一定的指导和影响作用;第三个层面更加具体,它指具体的生活方式,即所谓的风俗习惯。在文化研究的时候,应该从某个角度出发,对文化先进行定义。
文化研究的方法有两种:民族志(ethnography)和结构法。前者强调研究人去要研究的地方切身感受当地的文化,后者仅强调对文本的研究,通过研究目标语文本来看出目标国家的文化。一般采取的是后者。
文化和语言的关系是本次所要阐述的重点。在文化和语言的关系的研究上,西方显然比中国来得具体和科学。中国的文化语言研究发源的比较晚,而且方法大多数来源于西方。
西方文化语言学的研究鼻祖是洪堡特,他提出的语言相对论(linguistic relativity)对后来的文化语言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西方主要分成两派:一派是以Whorf为首的认为语言决定了文化的;另一派占少数,认为文化对语言的影响比较大。另一派的观点比较弱,他们从来没有提出过文化决定语言的说法。Whorf的假说是建立在大量的实证基础上的,他认为语言决定了人们的思维,让人们透过一个框框来看这个世界。但是他的观点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强一点的,认为语言完全决定文化的,另一个是相对弱一点的,认为语言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文化,但没有决定文化。这两个观点均由他提出,且有一定的偏差。虽然后来的学者对他的许多观点提出质疑,但他仍是至今为止处于统治地位的理论。但我认为,这种语言决定文化的观点,过多的强调的语言的决定性作用,而忽略的文化的反作用。很大程度上,受文化的影响,人们使用语言也会有很大的不同。
相比西方的文化语言研究,中国的研究没有那么系统,也没有什么根深蒂固的理论。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没有太多的去研究文化和语言是否有决定性关系。中国的学者大多集中在通过研究汉字来看出中国古代的文化的研究。需要说明的是,汉字比英文字母蕴涵了更多的文化。但是,大多数这方面的研究都太过于笼统。
总而言之,语言和文化的决定性问题,是属于“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只要明确文化和语言相辅相成的紧密联系便可。透过语言看文化却有很大的实际意义。比如,中国人通过分析西方人的语言,便能看出西方的思想,反之亦然。了解了文化和语言的关系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实践意义就在于能将其理论与教学实践相结合。
在某种文化中,语言的作用和该特定的文化对词汇习语意义的影响是无所不在的,以至于不仔细考虑其文化背景就很少能准确理解语言材料。因此,外语教学就不应脱离所学语言国家的文化和历史。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应正确处理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的关系,除了完成必要的语言知识讲解外,还应有意识地、适时适量地进行文化导入,这样既可以了解英语国家的文化,又可以通过文化的学习来促进语言习得,加深学生对语言的理解,使语言因赋予了文化内涵而易于掌握,在提高学生语言知识和综合运用语言的能力的同时,增强他们的文化素养和对文化的敏感性和洞察力。而且,英语中的听、说、读、写、译都离不开对文化背景知识的掌握,只有这样,才能更全面、更准确地理解目的语。
目前,在英语语言教学中导入文化的方法有如下几种:
1.直接注解法,即在某些有文化涵义的词或句子后面加上注释。学生通过阅读注释来了解背后的文化常识。
2.交互融合法,即将文化内容与语言材料直接结合在一起。学生在训练阅读或听力的技巧时也了解了一定的文化常识。
3.交际实践法,即学生通过具体的实践,与听说读等练习,以及直接和外国人交流来达到学习语言的目的。
4.比较法。顾名思义,这个方法要求老师在讲授文化知识的同时,加上中西方文化的对比,让学生比较中西方文化的特点,这样了解西方文化的同时,能够更好的了解中国人自己的文化。这个方法就需要教师对中西方文化都有一个透彻的了解。
除了以上的几个方法,我认为还有一种方法比较有用,即通过文学看文化。可以说,文学就是语言的一部分。文学不是脱离语言存在的,更不是语言的另一个范畴。语言是文学的构成,而文学作品则是语言的应用。语言和文学作品的关系就象砖瓦和建筑物的关系一样。它是由语言搭造而成的,语法、句法、词法等语言知识被灵活运用其中。另一方面,文学又是文化的一个部分,分析一个文学作品,必然要参照它的历史背景,艺术特色和哲学观点等。文化深深的嵌在文学作品中,所以,文学作品必然会反映出文化。所以,导入文化可以从文学的角度出发,通过阅读文学作品,分析作者的观点,以及作者所处的时代特点,及其所处的历史地理环境的特点。最典型的作品莫过于《圣经》了。可以说,英语语言文化发展至今,《圣经》的影响贯穿了始终,英美日常生活中的用语经常引自圣经的典故。学习了圣经,就可以理解很多其他地方出现的文化常识了。
目前的英语教学中,文化已被大大重视,多媒体以及网络的普及让学生有更大的机会可以在学习的语言过程中,学习文化。现在国内英语教学界比较流行的交际教学法实际上便是文化与语言结合一个典型的例子。交际法认为语言是用于交际的工具,学会一种语言不仅要学会掌握他的语言形式,更要学会具体运用,也就是说要知道在什么场合运用。知道在什么场合下使用也就意味着使用语言的人必须具备相当的文化常识。
总之,文化和语言密不可分。虽然还不知道也搞不清楚到底是语言决定文化,还是文化决定了语言,有一点是肯定的,即文化和语言是互相渗透、相互影响的。这对教学实践是有很大启发的,它告诉我们,教师在教学语言的同时,应该要同时进行文化的导入,这样可以更好地促进语言的学习。
参考文献:
[1]鲍志坤.也论外语教学中的文化导入.外语界,1997,(1:)7-10.